| 臺灣 | |||||||||
|---|---|---|---|---|---|---|---|---|---|
| 1895年-1945年 | |||||||||
| 地位 | 日本殖民地 | ||||||||
| 官方語言 | 日語 | ||||||||
| 常用語言 | 台灣閩南語、客家語、台灣南島語、文言文 | ||||||||
| 政府 | 殖民政府 | ||||||||
| 日本天皇 | |||||||||
• 1895-1912 | 明治天皇 | ||||||||
• 1912-1926 | 大正天皇 | ||||||||
• 1926-1945 | 昭和天皇 | ||||||||
| 臺灣總督 | |||||||||
• 1895-1896 | 樺山資紀 海軍大將(首任) | ||||||||
• 1944-1945 | 安藤利吉 陸軍大將(末任) | ||||||||
| 總務長官 | |||||||||
• 1895-1897 | 水野遵(首任) | ||||||||
• 1945 | 成田一郎(末任) | ||||||||
| 歷史時期 | 日本帝國 | ||||||||
• 馬關條約 | 1895年4月17日 | ||||||||
• 馬關條約生效 | 1895年5月8日 | ||||||||
• 日本殖民台灣時期 | 1895年-1945年 | ||||||||
• 日本投降 | 1945年8月15日 | ||||||||
• 台灣光復 | 1945年10月25日 | ||||||||
| 面積 | |||||||||
| 1905年 | 36,000平方公里 | ||||||||
| 1930年 | 36,000平方公里 | ||||||||
| 1940年 | 36,023平方公里 | ||||||||
| 人口 | |||||||||
• 1905年 | 3,039,751 | ||||||||
• 1930年 | 4,640,820 | ||||||||
• 1940年 | 5,872,084 | ||||||||
| 貨幣 | 臺灣銀行券、日圓 | ||||||||
| |||||||||
 | |||||||||||
|---|---|---|---|---|---|---|---|---|---|---|---|
| 史前時期 | |||||||||||
| 荷據 1624-1662 |
西據1626-1642 | 原住民政權及部落~1933 | |||||||||
| 明鄭時期 1662-1683 |
|||||||||||
| 清朝時期 1683-1895 |
|||||||||||
| 日佔時期 1895-1945 |
|||||||||||
| 台灣光復 1945 迄今 | |||||||||||
| 其他臺灣系列 | |||||||||||
台灣日佔時期,或稱台灣日據時期、日本殖民台灣時期[注 1],是1895年至1945年間日本殖民統治中國領土台灣的時期。
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始於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後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在統治初期,日本對台灣實施殘酷的軍事統治,遭遇了台灣人民的武裝抗爭。自大正時期後,日本對臺灣統治已漸趨穩固,日本殖民當局改取較為柔和的統治方式。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方因應戰爭需要更進一步推行全面性的皇民化政策,以期將臺灣人同化於日本。
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有許多台灣人赴大陸地區參與辛亥革命,及與國共兩黨合作抵抗日本統治;也有部分台灣民眾屈從於日本殖民當局的皇民化政策,改日本姓名,加入日軍參與日本的對外侵略。[1]
1945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10月,台灣的日本佔領軍向中國投降,台灣光復,回到了中國的懷抱。
馬關條約

1894年(清光緒20年),清帝國與日本因為朝鮮主權問題而爆發甲午戰爭。次年3月20日,戰況呈現敗象的清朝,派出李鴻章為和談代表,並以全權大臣身分赴日本廣島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議和,但談判沒有結果。最後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廷一方面被迫承認朝鮮獨立;另一方面也將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
臺灣割讓予日本的記載為馬關條約第二條之內:第二、割讓臺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第三、割讓澎湖群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間的各島嶼。另外,第五條亦有如下之文字:中日兩國政府於本約批准交換後,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員赴台灣省,實施該省之讓渡事務,但需於本約批准交換後二個月內,完成上述之讓渡。5月8日此條約生效,因為此條約,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該和談經過亦史稱台灣割讓或乙未割台,日本接收臺灣時遭遇數月的抵抗,也被稱為乙未戰爭。[2]
歷史沿革
自1895年6月17日日本殖民台灣開始,就遭遇了台灣人民頑強的抵抗,因此,為加大對台灣人民的鎮壓,日本當局選派「台灣總督」時,非常看重軍事履歷,通常以有中將以上軍銜的武官來擔任,例如首任為海軍大將樺山資紀,其後分別為曾任日軍第三師團長桂太郎、日軍中將乃木希典等。面對台灣人民的抵抗,日本殖民當局死傷慘重,經濟上毫無收益,國際形象也大受打擊,例如1895年軍費佔到殖民當局財政支出的54%[3]。因此乃木希典提出了「將台灣以一億日圓賣給法國」的言論。[4]
在日本國會,乃木希典的主張遭到兒玉源太郎的強烈反對,兒玉源太郎嘲諷乃木希典之所以無法統治台灣是因為他無能,並主動請求擔任第四任「台灣總督」,在台灣實行了新的殖民政策[4]。兒玉源太郎自1898年擔任「台灣總督」,任期長達八年,他上任後,一面加大了對台灣人民起義的鎮壓力度,殺害台灣人民數萬人;一面挑撥台灣人民的矛盾,實施連坐制度,逼迫台灣人民互相舉報「抗日分子」,親人、鄰居反目成仇。[5][6]
兒玉源太郎在甲午戰爭期間的老部下後藤新平在台灣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他對台灣的統治方式被稱為特別統治主義,後藤新平認為,殖民地人民無法被同化,因此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將台灣視為與日本本土不同的殖民地,不適用日本法律,例如,日本本土不允許售賣鴉片,但後藤新平卻在台灣實施專賣制度,將鴉片買賣權統歸殖民當局,藉此大肆斂財,鴉片專賣收入在「台灣總督府」1902年的財政收入中佔比高達42%,台灣人民深受鴉片之害。[5]在這段時間內,台灣總督於「六三法、三一法」的授權下,享有所謂「特別律令權」,集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於一身。[7][8]
1919年,第八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上任後,在時任日本首相原敬的支持下,實施了與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不同的統治方式,他們認為,徹底同化台灣是可能的,將台灣視為「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仍為內地之一部」,直接適用本國法律,這種思想被稱為內地延長主義。[9]
日本不滿足於殖民台灣,又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侵略中國大陸,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日本為了獲取資源用於戰爭,加大了對台灣人民的剝削壓迫和對台灣資源的掠奪。為此,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強迫台灣人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燒毀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道教。1940年,日本殖民當局公佈改姓名辦法,更進一步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日本當局開始強征台灣人民為日軍做軍需品運輸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殖民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強征台灣人民直接上戰場參戰。[10]
此外,日本殖民當局實施「慰安婦」制度,大多數「慰安婦」受害者是在遭到脅迫或欺騙的情況下被徵召,實際上被日本軍隊當作性奴隸,受到肉體和心靈的雙重創傷。[11][12]至今,這個事件仍被視為踐踏女性權利及尊嚴的行為,在21世紀仍有倖存的台灣「慰安婦」受害者對日本提出賠償的要求;直到2023年5月台灣最後一位台灣「慰安婦」受害者過世為止,仍未獲得日本官方的道歉。[13]
行政區劃
日佔初期,行政區劃變動非常頻繁,1895年,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設置台北縣、台灣縣、台南縣及澎湖廳,當年又將台灣縣、台南縣改為台灣民政支部和台南民政支部,澎湖廳改名為澎湖島廳;1896年,改為台北縣、台灣縣、台南縣及澎湖島廳;1897年,又改為台北縣、新竹縣、台中縣、嘉義縣、台南縣、鳳山縣、宜蘭廳、台東廳、澎湖廳共計6縣3廳;1898年,又改為台北、基隆、深坑、宜蘭、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斗六、嘉義、鹽水港、台南、蕃薯藔、鳳山、阿猴、恆春、台東、花蓮港共計20廳。[14][15]
直至1920年,改為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二廳(台東、花蓮),5州下轄47郡3市,2廳之下又分為8個支廳。1926年又增設澎湖廳以及台北、基隆、新竹、台中、彰化、台南、嘉義、高雄、屏東9個州轄市。到1943年,殖民當局在台灣共設置了5州、3廳、51郡、11市、56街、213莊。[14][15]
| 1943年行政區 | 人口(萬人,含下轄市) | 州轄市(括注人口,萬人) |
|---|---|---|
| 台北州 | 130 | 台北市(40)、基隆市(11)、宜蘭市(4) |
| 新竹州 | 88 | 新竹市(10) |
| 台中州 | 144 | 台中市(10)、彰化市(7) |
| 台南州 | 162 | 台南市(16)、嘉義市(11) |
| 高雄州 | 100 | 高雄市(22)、屏東市(6) |
| 台東廳 | 10 | 無 |
| 花蓮港廳 | 17 | 花蓮港市(4) |
| 澎湖廳 | 7 | 無 |
抗日運動
武裝抗日運動
在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中,武裝抗日運動主要發生在日本統治的前20年。根據一般學者的研究,武裝抗日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期是台灣民主國抗拒日軍接收的乙未戰爭;第二期是緊接着台灣民主國之後的前期抗日游擊戰,幾乎每年都有武裝抗日行動,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之後,台灣反日運動轉為維護中華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不過期間仍發生轟動全世界的霧社事件等武裝抗日運動。
根據後藤新平引述總督府報告,僅在1898—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日本領有台灣前八年,共有32,000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16]。
台灣抗日運動與中國大陸關係匪淺,福建是台灣人民抗日運動的主要資金和軍事裝備來源地,抗日武裝的領導人,如簡大獅、林少貓、林李成等,常在形勢緊張時逃往大陸,再伺機返回台灣;另有許多大陸人以「打工」的名義赴台支援。[3][17]
台灣民主國

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決定,在台灣住民中引起了軒然大波。1895年5月25日,台灣官民宣佈於台北成立台灣民主國,推舉巡撫唐景崧為總統。日軍在5月29日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6月3日攻陷基隆[注 2]。於是台灣民主國政府的領袖們,包括唐景崧和丘逢甲,都內渡逃亡至大陸。6月下旬,餘眾又在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總統,民主國雖和日軍發生不少規模不小的血戰。但到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內渡大陸,日軍佔領台南,台灣民主國政權至此完全劃下了句點。[2][18]
前期抗日游擊戰
台灣民主國宣告崩潰以後,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於1895年11月8日向日本東京大本營報告「全島悉予平定」,隨即在台灣展開統治。但是,1個多月以後,台灣北部原清朝鄉勇又於12月底開始一連串的抗日事件。而這一期的抗日可以說是第一期台灣民主國抗日運動的延伸。[19]
1896年,苗栗地區部分義軍撤往大湖,加入泰雅人原住民抗日行列。由「得磨波耐社」大頭目「北都巴博」率領,在馬那邦山區與日軍展開一場殊死戰。但日軍擁有山砲等重型武器。原住民4位頭目北都巴博、接卡久因、杜哈魯、莫拉邦、和義軍將領柯山塘及屬下全部陣亡,日軍陣亡七十多人。
中南部地區簡義、柯鐵虎、劉德杓為首的民勇。於1896年6月進攻駐守南投街及斗六街的日軍,7月進攻鹿港,辜顯榮率「別動隊」協助日軍。雖有部份「別動隊」成員倒戈,但民勇軍仍告失敗。事後,日軍在雲林地區展開清鄉報復行動,約六千至三萬人遇害,史稱雲林大屠殺。[20][21]
1902年,苗栗地區風雲再起,因原住民不滿歧視與壓迫且詐騙了山墾權,襲擊「南庄支廳」。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紛紛響應,交戰1個多月,史稱「南庄事件」。之後,日本人又殘殺逃到馬那邦山避難的難民,引起原住民更大規模抗日,雙方交戰好幾個月。
後期抗日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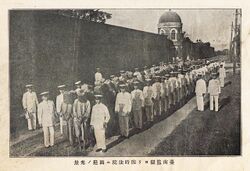
1902年,漢族抗日運動稍歇,直到1907年11月發生北埔事件,武裝抗日才進入第3期。[19]
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總共有13起零星武裝抗日事件。在這13起事件中,宣稱要將台灣復歸中國版圖的有4件,要建立封建王朝,自己稱王稱帝的有6件,兩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標的則有2件。[22]
這些事件中,有11件發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後,並且有4件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刺激而發動的。[22]1913年1月的苗栗事件領導人羅福星是中國同盟會會員,在大陸接受了軍事訓練,最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於1914年3月3日被日本殖民者處決。[23][24]
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是台灣漢族最後一次武裝抗日運動,規模浩大。領導人余清芳以「大明」為國號,建立大明慈悲國政權,並派人前往中國大陸召集同志支援,但最終仍被日本殖民當局消滅。[23]
原住民抗日運動

後期抗日運動中,以發生於臺中州能高郡霧社(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之霧社事件最為著名。這起事件是由於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長期的壓制傳統文化、歧視與勞動剝削,致原住民生活困苦、長年積怨。
1930年10月27日,以頭目莫那魯道為代表,共六個部落300多位族人發動抗日起義,殺死134名日本人,事件發生後,總督府主張對原住民擁有報復及討伐權。於此理念下,總督府遂展開近二個月的討伐,以賽德克人(當時被歸類於泰雅人)為主,參與反抗行動的三百名原住民兵勇非戰死即自盡,其家人或族人也多上吊或跳崖。史稱霧社事件及二次霧社事件,是台灣日佔時期最直接且最激烈的武裝抗日行動。[25]
社會運動
由於日軍的殘酷鎮壓及台灣民眾深刻地認識到民間武裝與日軍相比極為落後和弱小,且中國大陸處在軍閥混戰狀態下,無力援助台灣,故而自1915年以後,台灣幾乎不再有大規模的武力抗爭行動。台灣的知識分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持下,以非武裝的抗日手段,組織近代政治社團、文化社團和社會社團,採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識的宗旨,以此結合意識相近、志同道合的同志。[23]

1918年以來,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紛紛成立民間組織,其中尤其以1920年的新民會影響最大,拉開了這一階段各項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繼發起。日本殖民當局深刻地認識到,這些運動並非如名義上所說的只是在日本法律範圍內尋求自治,而有更深層次的謀求民族解放和回歸祖國的文化內核,因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以取締,1923年12月26日,殖民當局在全島進行大搜捕,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參與者一網打盡。[23]
1930年代中期後,在皇民化運動的指導下,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都徹底遭到日佔台灣當局禁絕。
參與大陸革命和抗戰
1897年8月,興中會成員陳少白在台北成立了台灣興中會,組織台灣民眾支援大陸革命。1900年,孫中山在發動惠州起義前來到台灣籌措軍費及武器,並與台灣分會的同志交流,失敗後經過台灣逃往國外。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1910年,孫中山派王兆培回到台灣發展革命組織。黃花崗起義參與者中有許贊元及羅福星(上文中提到的苗栗事件領導人)兩名台灣人,另有林薇閣給予了一些資金支持。[24][26]
1912年1月,台灣愛國詩人丘逢甲赴南京參加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會議,被選為參議員。[24]
全面抗戰爆發前,台灣民眾在大陸活動的主要地區為北京、上海、南京、廈門和廣東等大城市,主要活動內容是輿論上或政治上的,他們宣傳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人民的壓迫,並支援台灣抗日運動。[17]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許多台灣愛國人士前往中國大陸(或原本就在大陸活動的人士)參加抗戰,例如,李友邦領導的台灣抗日義勇隊,利用自身在日本統治下學習過日語的技能,在陣前開展對日軍廣播喊話。1940年3月,為了團結在大陸的台灣抗日誌士,各個組織在重慶成立了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1941年又改組為台灣革命同盟會。[17][27]
文化
文學

由於兩岸內在文化的同質性,新文化運動極大地影響了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發展,[28]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創立了《台灣青年》和《台灣民報》等期刊,開始創作白話文作品,將大量大陸白話文作品引入台灣,並與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文學家、思想家交流學習。這些擺脫古詩的近代文學,為台灣白話文運動的肇始者。[29]
這一文化運動雖然受到日本殖民當局的刻意壓制,但並沒有消失,反而愈發壯大。1936年,集結台灣進步作家的台灣文藝聯盟、台灣新文學相繼成立,這些團體表面上標榜為文藝團體,實際上則向民眾宣傳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反對日本殖民的思想。[23][30][31]
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聚焦於批判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揭露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的悲苦境遇,鼓勵台灣人民與日佔當局鬥爭,具代表性的作家有:賴和(《一桿稱仔》)、楊逵(《送報伕》)等人。[32][33]
電影
在日佔時期,台灣的電影被日佔當局控制,並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電影的影響,日佔當局在台灣出品的電影大多為普及日語、宣傳「總督府」政策、推動「皇民化」及進行戰爭動員。[34][35]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人民缺乏通過電影藝術表達自身思想訴求、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渠道,少數台灣人自製的電影實際上也無法擺脫日本殖民者的控制,因而票房慘澹,不受台灣觀眾的喜愛。[34]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大陸電影對台灣產生了很大影響,撫慰了台灣人民對祖國的思念,鼓舞了台灣人民的愛國熱情,許多台灣青年受大陸電影影響而前往大陸讀書,也有台灣電影工作者擺脫日本殖民當局的控制,前往上海學習電影製作,有的留在大陸投身中國自己的電影事業,有的將大陸電影帶回台灣傳播。[36][37]這一時期著名的台灣電影人例如第一位前往上海學習電影的台灣人張秀光,電影演員鄭連捷(鄭超人)、羅朋,電影劇本作家劉吶鷗等。[34]
大陸電影傳入台灣後,受到了台灣民眾的廣泛歡迎,票房不僅超過了歐美影片,也打敗了日本影片。[34]甚至有些電影院將歐美或日本電影以「大支那劇片」或「大中國上海影片」的名義來欺騙觀眾,吸引票房。[37]
但由於大陸電影的輸入受到殖民當局的阻撓,例如內容被審查、刪減,且輸入的均是3年甚至10年前出品的舊片,導致台灣人民對大陸的電影發展水平產生了一些誤解。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殖民當局對大陸電影的限制進一步加劇,要求「外語」影片必須以日語配音等,七七事變後,大陸電影在台灣幾乎被徹底禁止,少數輸入的影片也多為日本傀儡政權下出品的宣揚日本帝國主義的電影。[34][37]
1945年,國民政府收復台灣後,接管了原被「台灣總督府」控制的日本電影產業。[38]
京劇
殖民地時期的台灣京劇深受大陸影響,例如著名旦角演員梅蘭芳在台灣相當著名,並深刻地影響了台灣的京劇藝術,台灣京劇界將梅派視為旦角的正宗流派。[39]海派京劇在台灣日佔時期也有較大影響力。[40]
布袋戲
布袋戲是福建和台灣當地的傳統民間藝術,在清朝從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傳入台灣,[41]內容大多基於歷史故事或傳說故事改編,宣傳忠孝仁義等中華傳統文化精神,後來逐漸發展出以武俠故事為母本的新式布袋戲。[42][43]
1936年,日本殖民當局推行皇民化運動,幾乎禁止了布袋戲,藝人們或是改業,或是輾轉到大陸謀生。1941年,時任「台灣總督」長谷川清放寬了對布袋戲的限制,態度從禁止改為了利用,對布袋戲進行了日本化的改造,以去除其中的中華傳統文化色彩,人偶的服飾改為和服,配樂從中國傳統的鑼鼓嗩吶改為西洋樂。並將布袋戲改名為「人形劇」[注 3],其劇本常為水戶黃門、月形半平太等日式故事,傳統故事也被加入了宣揚武士道精神的內容。[44][45]
臺灣光復
準備
1944年4月17日,國民政府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研究台灣省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現狀,並據此提出收復台灣的方案,培訓接管台灣的幹部。該委員會翻譯了日佔台灣的文件共100多萬字,與在大陸生活工作的台灣人士召開座談會,了解日佔台灣的實際情況,最終決定採用行政長官制,於1945年9月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隸屬於國民政府行政院。[46]
1944至1945年期間,該委員會分別開設了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台灣警察幹部訓練班、台灣警察幹部高級訓練班等,為收復台灣蓄積了豐富的人才儲備。[46]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廣播投降詔書,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自此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年8月29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於9月1日於重慶市宣佈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同時命陳儀兼任台灣警備司令。9月9日,何應欽在南京接受岡村寧次對中國投降,並任命陳儀為台灣及澎湖群島的受降主官。[46]
10月7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副主任范誦堯通過廣播對台灣民眾宣佈國民政府將收復台灣;10月10日,台灣各界民眾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台灣省第一次國慶慶祝大會;10月17日,國軍第70軍陳孔達部抵達基隆港,受到當地民眾熱烈歡迎。[47]

受降典禮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時在台北公會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台灣總督」兼日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簽署降書後,由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遞交陳儀,雙方即完成受降儀式。自此,台灣和澎湖列島的領土、國民、行政管轄皆重歸於中國主權之下,這一天被命名為台灣光復節。主要參加人員有國民政府代表:陳儀、葛敬恩、柯遠芬、黃朝琴、游彌堅、宋斐如、李萬居,台灣人民代表:林獻堂、陳炘、杜聰明、羅萬俥、林茂生等30餘人,盟軍代表顧德里上校、柏克上校等19人。另外,還有日軍代表:安藤利吉及諫山春樹。[46][47]
註釋
參考文獻
- ↑ 論鍾理和文化身分的含混与轉化 (PDF). [2016-09-02].
- ↑ 2.0 2.1 許佩賢. 攻台戰紀-日清戰史台灣篇. 臺灣: 遠流出版社. 1995-12-20. ISBN 9789573227021 (繁體中文).
- ↑ 3.0 3.1 陳小沖.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1895——1904年). 台灣研究集刊. 1990, 04: 101–110.
- ↑ 4.0 4.1 日本曾想把台湾卖给法国. 文摘報. 2011年10月06日: 7.
- ↑ 5.0 5.1 許勇. 从“治理”台湾到“经营”满铁——儿玉源太郎与后藤新平的祸华事实. 世紀橋. 2009, No.178 (11): 45–47. doi:10.16654/j.cnki.cn23-1464/d.2009.11.004.
- ↑ Carl, G.H.; 吳玫. 日本入侵台湾的初期. 台灣研究集刊. 1984, (04): 85–93.
- ↑ 葉青. 日据时期“六三法”撤废运动与台湾知识分子民族联合阵线形成. 東南學術. 2017, No.260 (04): 212–218. doi:10.13658/j.cnki.sar.2017.04.026.
- ↑ 李理. “六三法”的存废与台湾殖民地问题. 抗日戰爭研究. 2006, (04): 45–61.
- ↑ 程朝雲. 台湾史话.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71–72.
- ↑ 劉蕾. 《朝日新闻》台湾青年参战动员研究(1937年-1945年). 新聞傳播. 2019, No.363 (18): 12–13+16.
- ↑ 薛洋. 让历史真相不被遗忘——台湾首座慰安妇博物馆揭牌. 兩岸關係. 2016, No.226 (04): 62–63.
- ↑ 朱德蘭. 台湾慰安妇.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09727195.
- ↑ 尹艷輝. 岛内最后一位“慰安妇”受害者去世,媒体人感叹:没等到一句道歉. 環球網. 2023-05-22.
- ↑ 14.0 14.1 褚靜濤. 台湾省行政区划的研议及光复初期的实施. 中國地方志. 2022,. No.332(03): 92–103+127–128.
- ↑ 15.0 15.1 於亞娟, 劉錫濤. 台湾历史时期行政区划沿革谈. 閩台文化交流. 2006, (04): 53–56.
- ↑ 楊, 碧川. 後藤新平傳. 台北: 一橋出版社. 1996: 62.
- ↑ 17.0 17.1 17.2 陳小沖. 试论台胞在大陆的抗日活动及其对台湾前途命运的思考——兼评所谓日据时期台湾人的“台独”运动. 台灣研究集刊. 2011, 115 (03): 64–73.
- ↑ 連橫. 臺灣通史. 臺灣: 眾文出版社. 1979-08-15. ISBN 9789575321864 (繁體中文).
- ↑ 19.0 19.1 王育德. 《台灣:苦悶的历史》. 2002-07-18: 312頁 [1979]. ISBN 957-801-203-9 (中文).(繁體中文)
- ↑ 許介鱗. 日本武士道揭謎. 日本綜合情報. 2004, (第5期): 頁104–119.
- ↑ 台灣記憶-簡義. Memory.ncl.edu.tw. [2014-08-15].
- ↑ 22.0 22.1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 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臺灣: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1946 [2022-05-05] (繁體中文).
- ↑ 23.0 23.1 23.2 23.3 23.4 劉紅林. 抗日归宗——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台灣研究. 2010, (No.103(03)): 60–64. doi:10.13818/j.cnki.twyj.2010.03.002.
- ↑ 24.0 24.1 24.2 郭海南. 台湾同胞积极投身辛亥革命. 人民政協報 (009). 2021-10-14. doi:10.28660/n.cnki.nrmzx.2021.007954.
- ↑ 高瑩瑩. 再论雾社事件与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活动. 台灣歷史研究. 2022, (No.3(02)): 32–42.
- ↑ 鍾紀東. 辛亥革命与台湾抗日起义. 台聲. 2021, 531 (20): 102–103.
- ↑ 魏慶. 台湾人民抗日斗争——中国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生力军. 軍事文摘. 2015, 347 (13): 56–58.
- ↑ 陳宇穎. 五四运动是台湾新文学运动重要指针. 團結報. 2009-05-02.
- ↑ 敬隱銘.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 魯迅研究月刊. 1999, (06): 17–20.
- ↑ 楊紅英. 论台湾文艺联盟活动之文化政治意义. 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 No.149(02): 63–67.
- ↑ 古繼堂. 台湾文艺联盟——三十年代台湾作家的大本营. 新文學史料. 1982,. No.(01): 161–164+172.
- ↑ 田建民.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7: 184–185. ISBN 978-7-03-051338-0.
- ↑ 田曉旭. 新文化运动在台湾. 中國青年研究. 1991, (05): 36–38. doi:10.19633/j.cnki.11-2579/d.1991.05.014.
- ↑ 34.0 34.1 34.2 34.3 34.4 高鈺涵. 日殖台湾时期两岸电影之间的关联. 東南傳播. 2022,. No.212(04): 31–35. 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2.04.025.
- ↑ 林豪. 日据时期台湾电影的社会教育探析. 當代電影. 2019,. No.279(06): 54–58.
- ↑ 呂訴上. 台湾电影戏剧史(上). 台北: 銀華出版部. 1961.
- ↑ 37.0 37.1 37.2 侯凱. 在银幕中看到“祖国”——大陆电影的在台传播(1924—1942). 當代電影. 2020,. No.291(06): 84–89.
- ↑ 侯凱. 影业接收、影片重映与影人迁徙——战后大陆电影对台湾电影的影响(1945—1949). 當代電影. 2020,. No.287(02): 71–77.
- ↑ 馮灼蘭; 簡貴燈. 别样梅香:京剧梅派艺术在日据台湾. 藝苑. 2019, 113 (05): 60–64.
- ↑ 簡貴燈. 日本侵占时期台湾京剧鉴赏的海派趣味.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福建師範大學,福建省社會科學院,台灣世新大學.兩岸文化深耕與融合——第五屆兩岸文化發展論壇文集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7.
- ↑ 杜曉傑. 台湾布袋戏起源及流派考. 民族藝林. 2014,. No.275(04): 18–23. doi:10.13767/j.cnki.cn64-1011/j.2014.04.002.
- ↑ 李恆. 台湾布袋戏的溯源传承与现代发展. 戲劇文學. 2016,. No.396(05): 136–140. doi:10.14043/j.cnki.xjwx.2016.05.028.
- ↑ 謝珍珍. 台湾传统布袋戏研究. 北方音樂. 2015, 35 (14): 17–18.
- ↑ 杜曉傑. 政治权力介入与台湾布袋戏的内台化转型. 藝苑. 2020,. No.117(03): 91–95.
- ↑ 陳秀免. 台湾布袋戏服饰演变的三个阶段及其启示. 武漢紡織大學學報. 2020, 33 (01): 71–74.
- ↑ 46.0 46.1 46.2 46.3 陳在正.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与台湾光复.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1–15.
- ↑ 47.0 47.1 陳立文; 鍾淑敏; 歐素瑛; 林正慧.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五卷:台湾光复研究.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ISBN 9787305148347.